Films


Adolescence
Love, intricate or straightforward, begs the question: what's the point of constant restraint and vigilance?
3 mins・2022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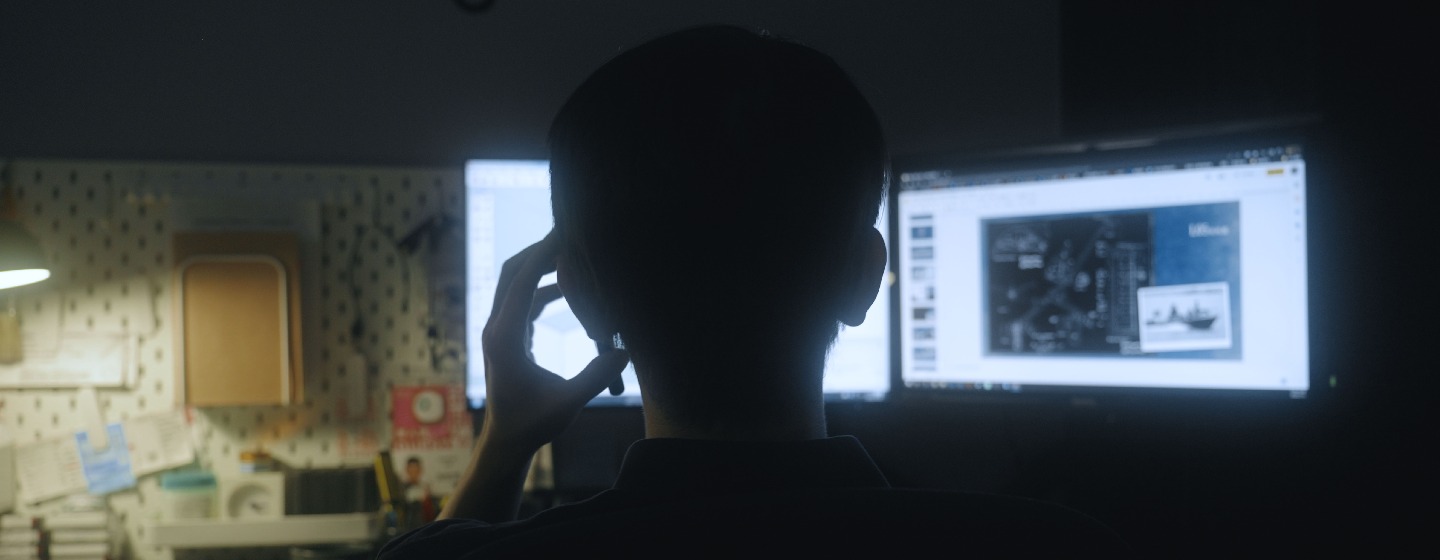
Unspeakable
In a future of AI-generated images, Jieliang effortlessly crafts his work until curiosity prompts him to ask: "What would my death look like?"
3 mins・2022

Agent Beyond Budget
A action film shoot turned into a life-and-death showdown between the entire crew and the director.
24 mins・2024
Related Notes



